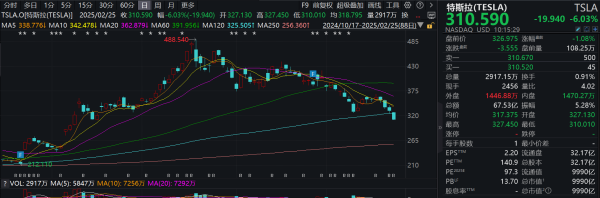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国内十大配资平台
嘉靖帝登基的那一年,几乎没人看好他能在这个位置上稳坐太久。即使如此,三年之后,他用一百八十根命杖彻底打破了所有的质疑,向天下宣告了谁才是那个真正的天子。
回顾历史,1521年,明朝的武宗朱厚照突然去世,没有留下继承人。皇宫内一片空白,京城内所有人都保持沉默,不敢轻举妄动。第二天,内阁首辅杨廷和紧急召集了六部九卿,商议立兴献王之子朱厚熜继承大统。这是内阁的决定,不是太后的意见,也不是宗室和百官的主张。朱厚熜虽然并非嫡子,他是明英宗的庶长子,封地在外。尽管从宗法角度来看他具备继位资格,但从礼制上讲,他必须与亲生父亲断绝关系,过继给孝宗,才能继位。
展开剩余83%然而,问题正是出在这里。朱厚熜进京三日,住进奉天殿,他清楚表达了自己不愿意与父亲的关系断绝,拒绝认孝宗为父亲。这些话虽然没有当面说出口,却在宫中流传开来。大家都知道,这场争斗才刚刚开始。
1522年春,礼部起草诏书,将朱厚熜称为“皇侄”。面对诏书,朱厚熜在御座上足足看了半个时辰,既没有批准,也没有斥责,只冷冷地说了一句:“改了再送。”第二天,礼部尚书毛纪因拒绝修改称谓和不肯下跪,请辞,第三天便被罢免。接下来的三个月里,五十多名大臣纷纷上疏,坚持祖制,要求遵循传统。杨廷和亲自撰写了奏疏,言辞严厉:“承大统者,应承宗祧,不能有所私情。”然而,嘉靖帝依旧不为所动。
外廷传言,嘉靖每天的生活就是读书、抄经、祭祀自己的父亲——兴献王,而不是孝宗。到了1523年,嘉靖终于忍无可忍,他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。命张璁、桂萼重新起草诏书,将生父称为“皇考”,这实际上是推翻了明朝开国时确立的礼制。杨廷和再次进谏:“不可私父称皇。”但朱厚熜始终沉默,只让杨廷和“退下休养”。这是明面上的罢相,实则内廷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分裂。以杨廷和、夏言、杨慎为首的老一派,坚持皇统优先;而张璁、桂萼则代表了支持嘉靖的“新党”。大家都知道,这场争斗注定不会仅仅止于书面上的争论。
1524年7月,朱厚熜发布一道圣旨,明确将生父兴献王尊为“睿宗献皇帝”,母亲为“章圣皇太后”,并命太庙供奉祭祀。此举不仅是对杨廷和派的挑战,更是向整个朝廷宣战。7月12日,诏书送出,第二天,给事中史孟麟率先上疏反对。嘉靖帝毫不犹豫地批示:“不准。”接下来的几天,数十份奏折陆续送到奉天殿,均无一人支持。7月14日凌晨,左顺门外跪满了220多名文官,全部衣冠整齐,伏地如磐。杨慎带头高喊:“陛下应以天下为重,不可悖逆祖训。”此时,禁军和太监均不敢出手阻止,宫中只剩下滔天的哭声。
然而,朱厚熜没有做出回应,只命人拉下帘子,自己悄然坐在帘后,听着文官们的诉求持续了五个小时。直到傍晚,诏令终于下达,命令即刻执行:“四品以上停职待命,五品以下交锦衣卫处理。”这是明朝中期最冷酷的一道命令。锦衣卫随即行动,王元春带领队伍冲入左顺门,手持廷杖,命令百官分列跪伏,宣旨后立刻开始行刑。那天的大雨让泥地里血水与脚印混杂,场面惨不忍睹。命杖虽是铁皮包裹,但每一棍落下,骨裂的声音清晰可闻。最终,180余名官员受杖,17人当场死于刑下,尸体堆积在东华门口,直到深夜才被抬走。杨慎满脸鲜血,牙齿尽失,昏迷三日后被流放云南,史称“折骨如薪,十不活一”。这一夜,反对的声音彻底消失。
朱厚熜冷冷地说道:“从今日起,不许再言礼议。”左顺门血案后,朝堂空了三日,没人敢议政,没人敢再跪。7月25日,张璁和桂萼进殿,奏请定献皇帝庙号。嘉靖点头,只淡淡说了一句:“睿宗。”八月初七,太庙增设了祭祀室,并在新主庙前张贴匾额,正式供奉新主。历史的篇章也随之改写,朱厚熜从此被尊为“世宗睿皇帝”。
嘉靖三年,张璁与桂萼先后担任首辅,迅速重用与自己立场一致的官员,改变了整个内阁结构。所有支持嘉靖的人都无一反对称父为“皇考”,礼部也开始重新修订祭祀仪轨,历史资料也被张璁指示进行改动,原本的“继统”被改为“嗣位”。全国官学讲堂的讲义也随之更改,任何不执行的新法的官员都将被流放,甚至在南直隶、浙江、福建等地,仍有官员抗命,最终被削职流放。
曾经站在朝堂上反对的老臣,如杨廷和,最终都选择沉默。而新的权力结构已经彻底定型,皇权的强势,彻底压制了文官的声音。这个夜晚,史书冷静地记录:“群臣伏阙谏,不纳,遂杖。”没有人再问为什么跪,甚至没有人再提“孝宗”的名字。
嘉靖帝统治期间,不仅改变了太庙的制度,重塑了官场结构,也通过每一步的决策,践行了自己的意志。他的胜利不仅仅是在称号上的改变,更是对历史制度的颠覆。文官阶层逐渐沉沦,士风的变化让曾经的“直言敢谏”成为了一句空话。
发布于:天津市加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